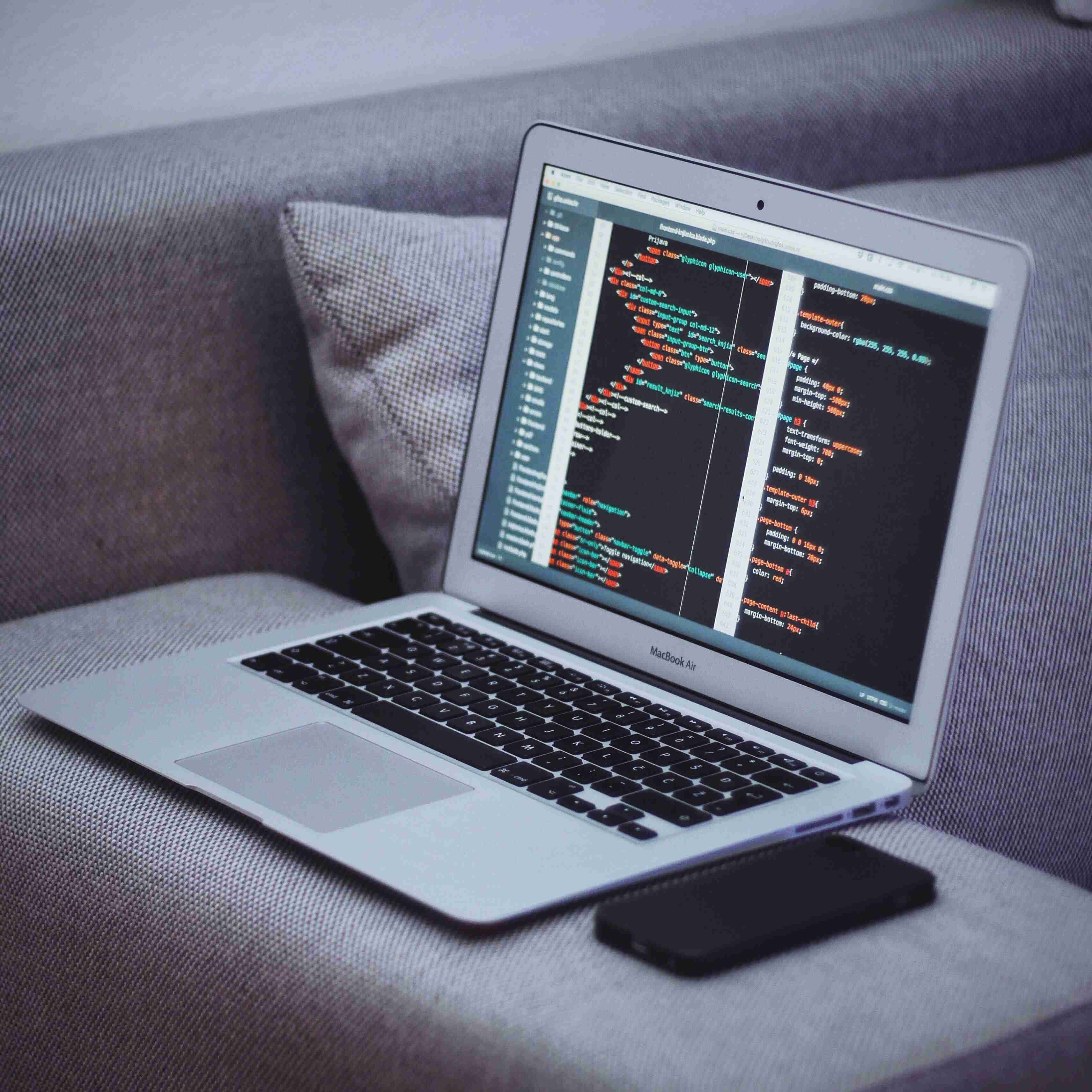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日]冈崎雄儿著,李玲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288页,49.00元

聂耳塑像
二、不足之处
(1)后见之明
罗志田曾指出,当前民国史研究有“倒放电影”倾向,由于已知结局便可发现当时人未能注意到的影响大局的关键性事物,却也容易有意无意地以后来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四期)。在本书中,作者提及1933年2月9日,由共产党的电影小组筹划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聂耳当选为执行委员。作者因此评论,“聂耳当时21岁,他不负众望,被业界视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这似有以后见之明过度赞誉之嫌。1933年9月,聂耳病后带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回制片厂上班,11月14日记写下养生细则,作者据此写道“大纲和细则规定了饮食、运动和卫生,连艺术活动都规定好了,不愧是‘聂耳流’的生活方式”(《聂耳传》,123页)。“不愧是”显然将聂耳置于一个较高位置;且什么是“聂耳流”?这种表述也许是翻译问题,实让人不知其意。
因为后见之明,在描述过往之事时,也往往加入现实的想法,造成时空错乱之感。笔者且举出书中两例。1921年夏季,同学邀请聂耳一起到水渠里游泳。来到水田地带后同学不慎溺水,不会游泳的聂耳蹲在水渠边上尽量靠近落水者,只是突然脚一滑,也落入水渠中。两人大喊“救命”后幸得一位路过的农夫伸出锄头将他们拉上岸(《聂耳传》, 17-81页)。这件事被作者解读成“似乎预示着聂耳将来不祥的‘命运’”,这种释读在后见之明外甚至有宿命论的意味。作者还提到一件事,1928年冬天,聂耳应征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成为学生兵,从云南到越南再到中国外省的途中,他见一位女孩被火车撞倒。女孩因家境贫苦,每天坐火车到小龙潭捡煤渣换钱,为省钱她每次都扒在车厢连接处无票乘车。那天被越南乘务员发现后便被扔下火车。对此,作者评论聂耳“同情那个为贫穷家庭吃苦卖力的年幼生命,他痛恨对贫民视若无睹的政治。看着这个对穷人苛刻残酷的社会,不断涌出的反叛之念塑造了聂耳‘人民音乐家’的立场”。须知“人民音乐家”是后来人给他封的称号,用在这里并不合适,至少他当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人民音乐家”。
(2)材料解读
聂耳升至中学后,曾写作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他写道:“我的人生观,非是宗教家的、哲学家的、以及科学家的……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我觉得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 或是译者问题,“对于学术上有研究”的原文为“对于学术上有(多番的)(点)……”(《聂耳全集》增订版[中卷],2011年,第3页)作者随后写道,批改作文联合中学的老师大概不喜欢这篇早熟的文章里有“政府的支配”字眼,所以给了一个略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聂耳传》,21-22页)很明显,老师是希望作者志存高远、积极入世,而并非是由于“政府的支配”这一字眼。
1933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左翼运动,新兴电影公思和艺华影业公司均受到国民党直属的内部组织蓝衣社的袭击。1934年1月,联华公司为自保,开除了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的聂耳。作者写道,聂耳“没有了固定工作,经济情况应该变得窘迫,但是聂耳日记上却写道‘最近收入颇丰’,大概是在被解雇前领导到了公司的欠薪和双薪(当时的月薪是30元),加上稿费和演出费等临时收入”。作者得出这一结论,却未给出证据或资料来源,随后只是援引1933年10月19日聂耳入不敷出的收支情况,说明“临时收入虽能对付一时,稳定收入来源对聂耳来说是很重要的”(《聂耳传》, 125页),显得仓促而欠严谨。
(3)叙述断裂
也许是本书定位为“传记”,其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过程着墨较少,尤其是讲完此曲在抗战时期广泛流行后,便直接跳到1949年被确定为代国歌,中间缺失了抗战结束后此曲被传唱和禁唱的过程,叙述因此断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试图对此部分展开分析,认为此曲在抗战结束后为国共两党分别利用,进而两党态度日渐分殊,共产党日益重视,逐步掌握其解释权,而国民党则加以禁唱(《在政党与国家之间:〈义勇军进行曲〉接受史》,《史林》2019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被确定新中国国歌便不再显得“突兀”或“理所当然”。
三、延伸思考
作者以有血有肉的事例,呈现了聂耳个人经历对其歌曲创作的影响,以及时代变局下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其逝世后,作者将眼光聚焦于由其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构成本书第五章内容,追溯了此曲在抗战时期广泛流行,随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过程,这显然是关于聂耳“神话”的最重要部分。只是,既然已将眼光放到他逝世后,那么这之后人们对他的种种“言说”同样值得关注。
1936年起聂耳被当作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奠基者”不断为人所提起。1936年,在聂耳周年祭之时,周钢鸣刊文指出,新音乐运动旨在将一切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集中在“国防音乐”阵线上,用音乐唤醒大众。“在聂耳死去的这一年中,中国新音乐运动正是循着他开辟的大路迈进”,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歌曲及进行曲,诸如《打长江》《打砖歌》《开路先锋》《卖报歌》《大路歌》等,“扬溢着一种铿锵的叫喊和活泼的节奏,像从地底发出来的巨人底吼声,像《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我们民族解放斗争进军的喇叭了”(周钢鸣:《论聂耳与新音乐运动——为聂耳周年祭而作》,《生活知识》1936年第二卷第五期,281-285页)。同年11月20日,麦新、孟波编选《大众歌声》(大众歌声社,1936年)即是献给“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聂耳和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其中收纳了聂耳遗作《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自卫歌》《开路先锋》等,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华民族不会亡》《救国军歌》等。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