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怀学是云南摄影界的一名“高人”,这里的“高”不仅仅是摄影功力,也指他身高1.93米,这两点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身高,80年代他在云南省体工队训练篮球,去外省打比赛,与队友一起为家乡争光;而真正让他觉得为家乡做了一件大事的是——凭借一己之力,拍摄出一本摄影画册《故乡》,260页,捧在手里沉甸甸。

2006年11月,金沙江上最末一级水电站——向家坝电站正式开工建设。淹没前的绥江老县城,依山而建,临水而居,与四川的屏夷司隔江相望,绥江新城将在老城旧址后靠500米的后山重建。

2004年2月,绥江风岩湾。金沙江上的现代导航设施——信号站,也叫“航标站”。金沙江下游河段,江窄、弯多、滩高、水急,航道部门在弯急水险河段建有信号站,为上下船只导航。

2012年8月,绥江下码头。男子坐在江边丢弃的沙发上,望着不远处搬空的绥江县城和眼前滔滔的江水发呆。对岸是屏山县屏夷司,是当年马湖彝族土司府的宗族属地。
![]()
2008年6月,绥江新滩镇石灰码头。过去,金沙江下游陆路交通不便,老百姓的日用百货、油盐酱醋,出入货物全靠水路运到码头,再人背马驮背往乡村,背夫行当生意红火。

(左)2012年8月, 绥江下码头,准备过河的四川拾荒村民。(右)2012年8月, 绥江下码头,转运家具到码头的村民。

(左)2009年9月, 绥江新滩镇。2008年底,新滩镇临江老街先期拆除。拆迁队将推倒的房屋废墟转包给移民自行破拆,拆下的钢筋归移民自己,双方各得其所,不再另付费用 。

2009年9月, 绥江新滩镇。新滩新镇还在建设中,老街一天功夫被夷为平地,成为电站库区内第一批拆除的建筑物。

2012年8月,走在绥江大桥上的男子,眼前是曾经的商业街区——金江街,瓦砾遍地,满目疮痍。绥江大桥,平时是县城的交通要道,赶集天,是热闹的场口,夏天,是纳凉的去处。

2012年8月,绥江红太阳广场。一个月后,毛主席塑像在简单的拆除仪式后,顺利吊装并运往新县城,待新县城建好后,择吉日重新塑立。

(左)2012年8月,屏山西正街。拆来只下剩框架的榫卯结构民居,仍然稳稳当当伫立在江边。(右)2007年11月, 绥江石龙殿。坐在拆得只剩墙基的自家堂屋中留影的老人。老人说:一年前丈夫走了,家里没男劳力,儿女又不在身边,这家,只有老婆子一个人一点一点慢慢搬了。

(左)2012年8月,绥江进场公路。查看停电的男子。上万移民搬入新城,停水停电不可避免。(右)2012年8月,绥江大桥头。冒着烈日顶着桌子走出拆除工地的男子,能抢出一样是一样。

2010年9月,绥江回望乡。下葬前,亲人和逝者作最后的诀别。电站蓄水前,库区移民家里亲人去世,都往淹没区380米水位线以上的后山上安埋,免得将来再次动迁,动了风水破了运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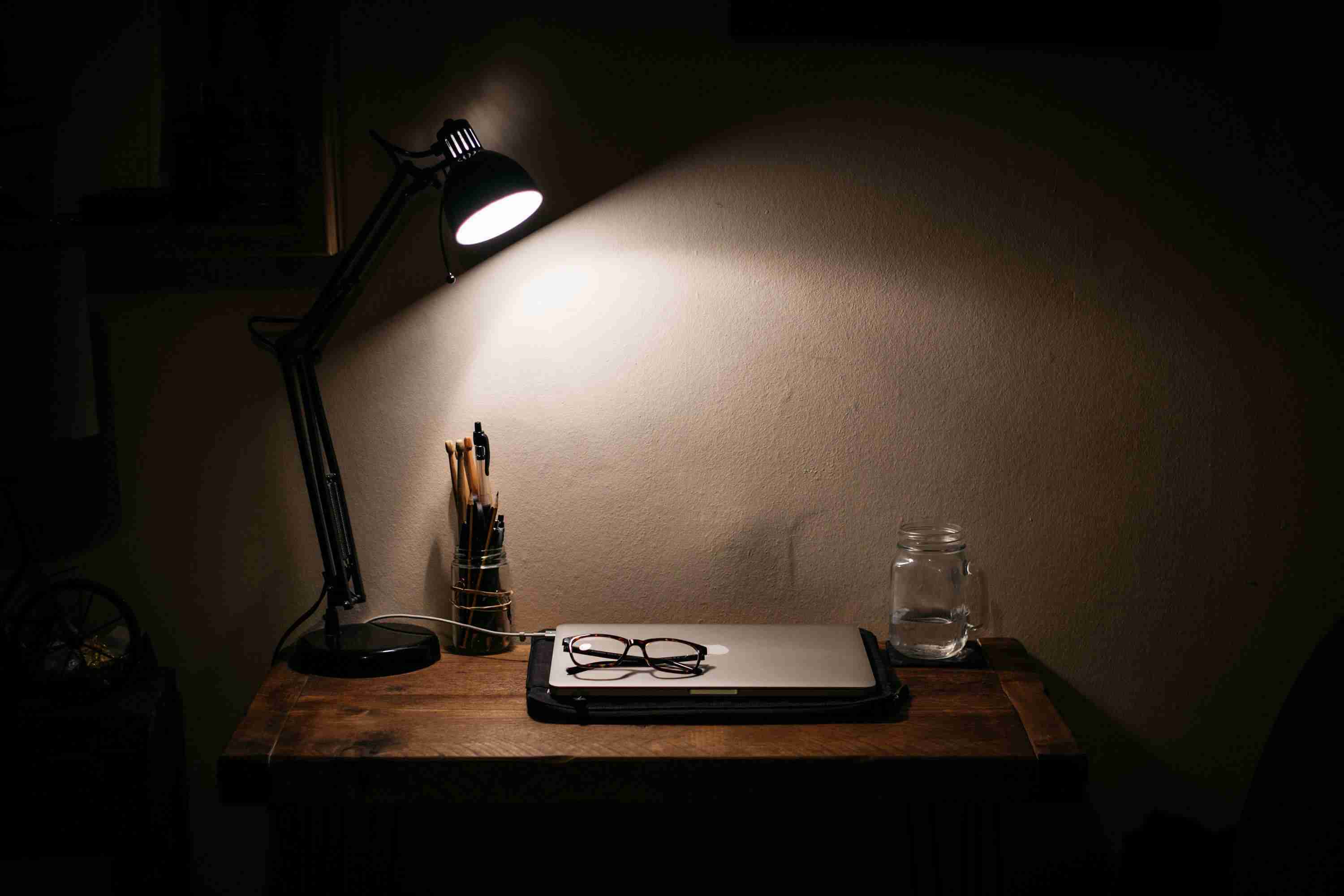
2012年8月,屏山大十市,疯狂寻找主人的丧家之犬。

2012年6月,屏山大十市。坐在搬空的自家门前,演奏《梦驼铃》的屏山县自来水公司退休工人唐德清师傅。拉得一手好琴,是县城红白喜事礼仪队的大提琴手。

(左)2010年9月,绥江下码头。码头上等待过河的年轻女子和老人。老人为联系不上对岸家人而焦急不安,女子掏出手机为老人联系上亲人,神情自若继续候船。

(左)2008年6月,绥江建设坝。罗燕抱着双胞胎女儿,坐在“双福临门”的门前留影。她说:以后告诉女儿,这是淹没前的老家。

(左)2012年6月,绥江小溪沟。农贸市场无暇顾及孩子的屠宰店女店主。(右)2007年11月,屏山下码头。女人从男人手中抢过小猪奔向码头。

(左)2010年12月,绥江新滩镇。看着肉架上没卖完的猪肉,蹲在老街上的肉贩,一筹莫展。(右)2009年2月,绥江金江街。年三十,金江街上兜售河鱼的鱼贩与买主讨价还价。

2007年,绥江县城碾子湾,祖传三百年的张氏杆秤作坊,用料真、手艺好,代代相传。如今,用杆秤的人少了,材料贵、成本高,只能勉强维持。姑嫂俩发誓:搬迁后再不做杆秤了。传承三百年的手艺将从此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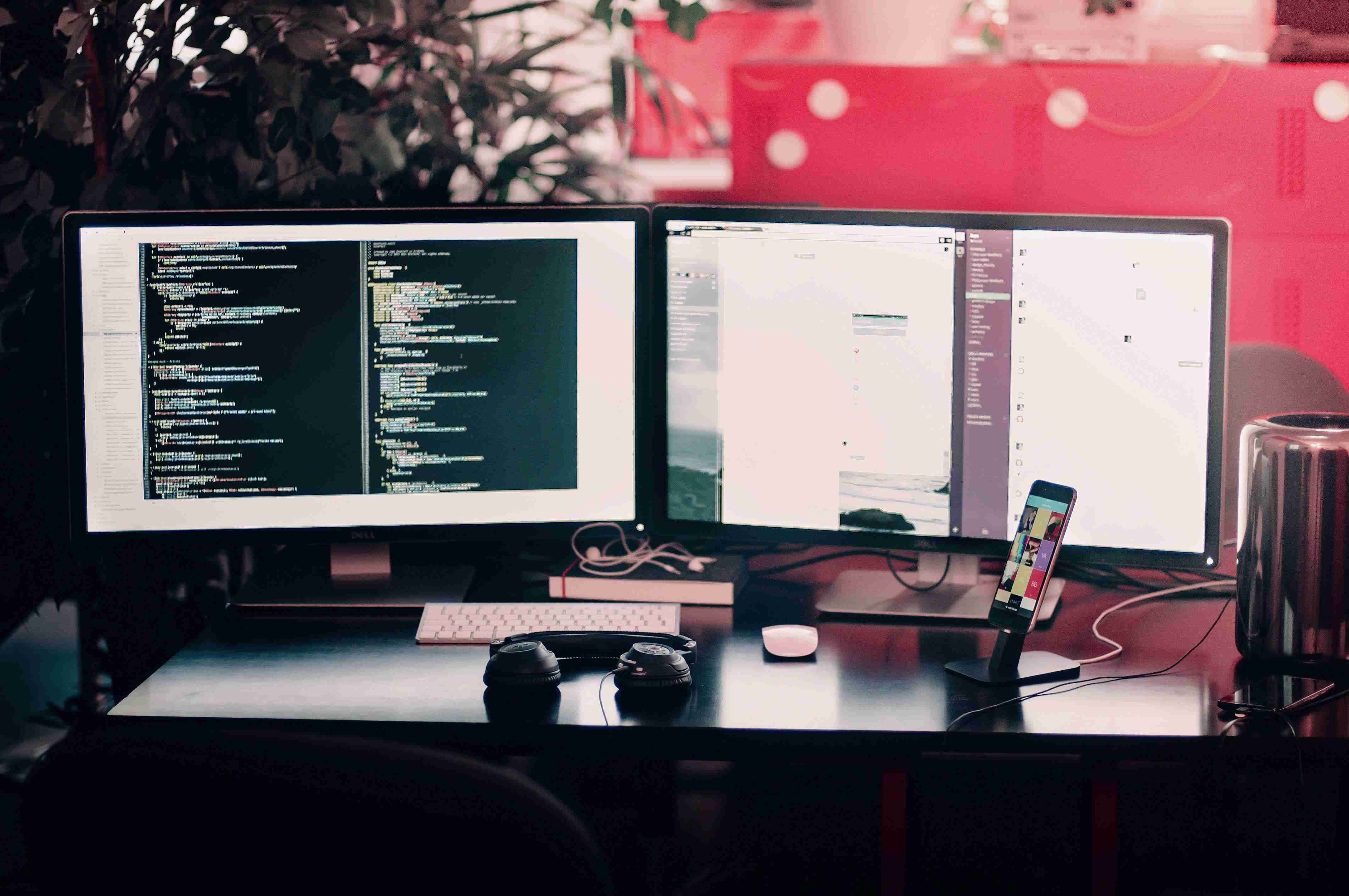
2011年7月,屏山新市镇。茶馆里喝盖碗茶的老者。泡碗茶,一蹲半天,喝到散场。

2009年9月,新滩石灰码头。每逢夏季的赶场天,散场后,这名卖完菜的男子,都会来到新滩石灰码头江边洗个冷水澡,凉凉快快回家。

2010年12月,屏山拖船垭。王发雄,从小在金沙江边长大,水性过人,打渔为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十年前,一条驳船在湾湾滩打烂,搁浅江边,反扣江中,他用氧焊割开船体,只身潜入船舱,将被困船工全部救出 。

2007年11月,绥江后坝小学。放学后,在绥江新城场平公路上比赛滚铁环的学生。农村的孩子没什么玩具,许多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2014年4月, 水富邵女坪。周光祥、夏仲英夫妇,库区自行安置移民,用补贴款加上自筹资金,在水库边盖了栋砖房。在县上读初、高中的儿女正是花钱的时候,夫妇俩农闲出门打工,供孩子上学和贴补家用,农忙回家种庄稼照顾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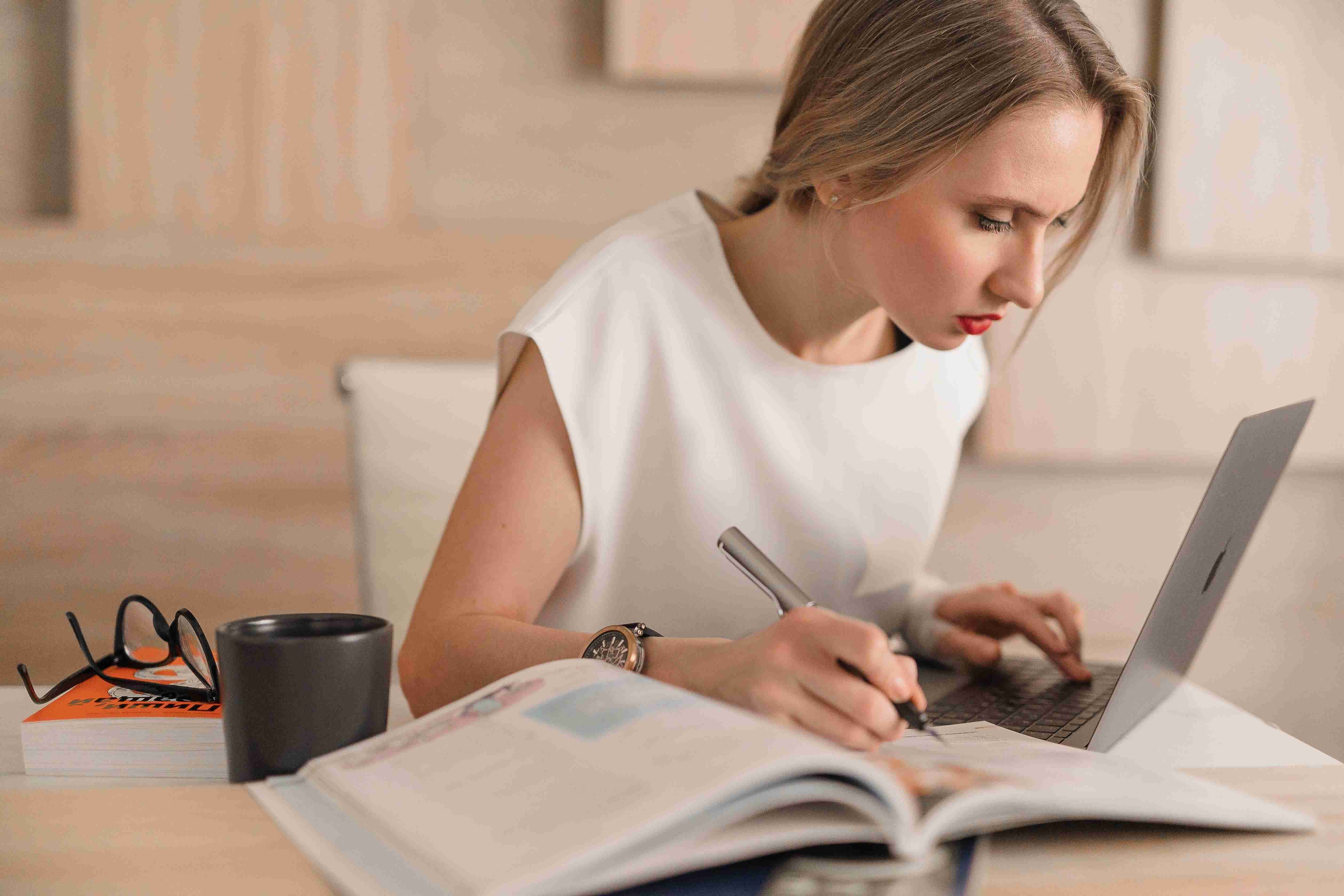
(左)2012年8月,挑着“天锅”的男人,走在已有移民入住,却仍在建设中的绥江新城。(右)2012年6月,绥江新县城还在昼夜抢建,向家坝电站库区移民搬迁工作已全面启动。许多移民才拿到毛坯房,墙体未干来不及装修便搬家入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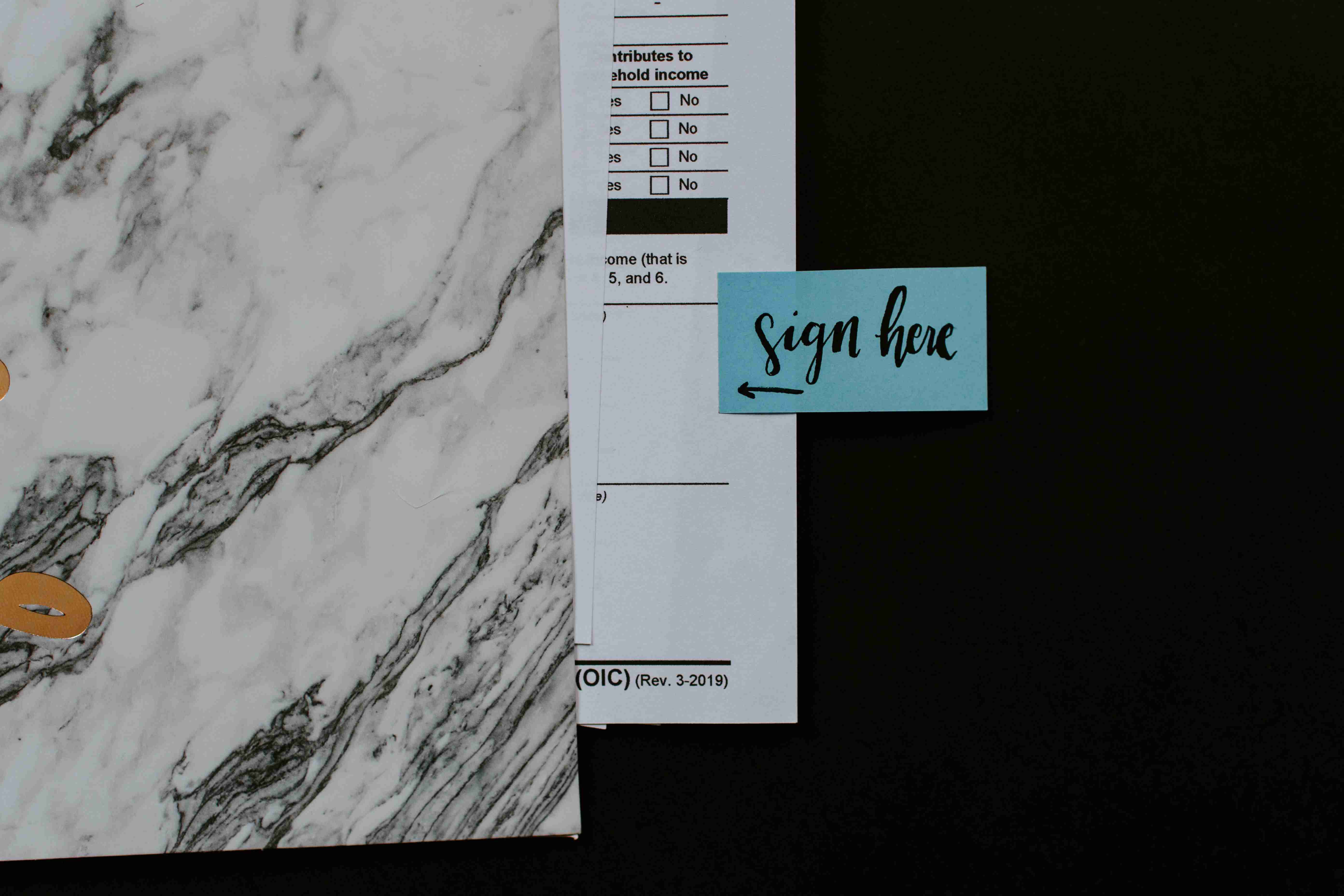
2012年8月, 绥江龙行大道。绥江新城街道还未铺装,搬进新家的移民迫不及待逛新城。

2014年4月,绥江杉木沟。蓄水后的湖边卡拉OK大家唱茶摊,活跃着一支“金江号子”演唱组合,传承金江文化。炎热夏夜,茶摊座无虚席,白天生意少时,成员们凑拢来,吊吊嗓子,吼两曲金江号子。每次县里的大型文艺演出,演唱组成员都会应邀登台亮相,一展歌喉。

2016年3月,绥江华峰村。两个诵经求神保佑的婆婆。在绥江新城小汶溪大桥头,老百姓捐钱建了个山神庙,供奉着险道、土地等神。每到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们会来求神拜佛,祈求平安。

2014年4月,绥江杉木沟。罗云(右),银行白领,一有时间她会到湖边游泳锻炼。

2014年4月,绥江罗家坪。远处露出水面的湖心岛是当年的湾湾滩,中华鲟的集中繁衍河段。如今,中华鲟再也无法洄游产卵,许多鱼类的生活习性都将被改变;不远处,渔民在湖上摸索新的捕鱼方法;眼前,喜鹊窝下的水域覆盖的是过去的新滩古镇,早已沉入湖底。在人神新拓的息壤之上,两岸百余里湖畔,将是移民永恒的故乡。
7、有没有什么类似关于纪录熟悉感的作品影响过您的创作?您的摄影美学来自哪里?
罗:有,那个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内摄影师,如:吴家林、侯登科、于德水等代表那个时代的一批摄影家,他们的摄影作品,把根深深扎在中国的乡土里,散发着泥土味和烟火气,不同程度影响过我。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摄影师,因为资讯等原因,几乎无法接触外国优秀摄影师的作品,后来随着中国摄影的“两报两刊”(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不断推荐国外的摄影师的摄影作品,如:萨尔加多、尤金史密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大师,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着我。我没正经学过摄影,不懂多少摄影美学,如果说我的摄影作品里真有美学特征的话,除了向这些我喜欢的摄影师学习外,恐怕更多的是来源于个人的人生经历,来源于曾经的乡野生活。
8、纪实摄影在西方得以长时间,较全面的发展,并达到一个高峰,然后随着电视媒体的冲击而缓缓沉寂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生活”杂志,包括今天的马格南都可以观察到。在中国,随着八十年代国门打开,我们是与西方“中断”了摄影的关系,但随着90年代纪实摄影在中国蓬勃发展了十几二十年,赶上了一个尾巴,然后在2000年之后又被当代艺术所裹挟,被资本所左右,您作为纪实摄影这一脉络过来的摄影师,对于今天的摄影,您怎么看当代艺术语境下的纪实摄影?它有没有影响或者未来您会调整自己的拍摄方式吗?
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纪实摄影(更确切说是传统纪实摄影)发展最好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优秀纪实摄影师,作为晚一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摄影人,揪住时代的尾巴,搭上最后一趟末班车,刚上车,还没来得及踩脚油门,就一头掉进了汹涌的当代艺术大潮,呛水是难免的。进入2000年,特别是近十年,纪实摄影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近几年炙手可热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阮义忠人文摄影奖”最终评出的大奖作品就能看出端倪,两大赛事的大奖一经出炉,都打上了当代艺术的烙印,都有观念摄影的影子,媒体一片哗然,质疑声不断。有质疑、有争议,很正常,是好事,说明传统纪实摄影不是铁板一块,不能改变,非把马格南奉为正宗才是纪实摄影。艺术贵在创新,传统纪实摄影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顺应摄影潮流的发展才能继续走下去,走得更远,并发扬光大。
我拍照片最常用的工作方式就是融入其中,只有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同悲同喜,同苦同乐,建立相互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你才能拍到真实感人,有温度的照片。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