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旅顺口大型画传 今天
在沈阳法库西北20公里处,有一个四家子蒙古族自治乡公主陵村。
苍穹下,一座5米多高的青石蟠龙碑伶仃矗立;碑身下残破的石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荒凉与寂寞。150年的风雨也许并不算是古老,碑上的刻字仍清晰可见:荷三朝之宠眷,经百战之勋名……督师五省,侵寒耐暑;临阵六年,奋爪士以同仇……这是清同治皇帝的圣旨。
清王朝最后一位横刀立马的王公——成吉思汗的第26代侄孙——僧格林沁亲王,曾经葬于此地,如今唯石碑独存。
放羊娃当上铁帽子王
清时,今法库县巴虎山以北地域隶属于科尔沁左翼王旗的世袭领地。公主陵一带是科尔沁左翼王旗的王室家族墓地,僧格林沁作为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死后葬到这里,也算是按章办事。
僧格林沁生于嘉庆十六年,父亲是科左后旗台吉家族的四等台吉。台吉,据说是源于汉语皇太子、皇太弟的称呼。僧格林沁虽拥有高人一等的台吉身份,可到了他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当时人都戏称僧格林沁的父亲为“雅玛台吉”,蒙古语意为给人放羊的台吉。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读书不多,很小就跟随父亲到别人家放羊。
后来,僧格林沁的族伯、科左后旗第九任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因膝下无子,便选了仪表非凡的僧格林沁为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爵。由于僧格林沁的养父娶了道光皇帝的姐姐,他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皇亲国戚。
道光五年,15岁的僧格林沁袭郡王爵位,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24岁时,被授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25岁时授镶红旗蒙古都统,成为统领一旗之士的年轻将领。
道光30年,40岁的僧格林沁奉命在京郊密云县剿匪,此战,僧格林沁谋局布阵,亲冒箭矢,一举剿灭悍匪,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华。
咸丰即位,僧格林沁成为顾命十大臣之一。咸丰四年,僧格林沁因功被晋封为亲王,并诏世袭罔替,就是铁帽子王。咸丰七年,僧格林沁任钦差大臣。咸丰九年,僧格林沁指挥大沽口海战,大败英法联军。步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僧格林沁亡我大清亡
僧格林沁护卫大清,可谓忠心耿耿。
咸丰三年8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京畿重地。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僧格林沁,命其率军进剿。僧格林沁不负众望,先是率军在天津南一战击溃太平军林风祥部,迫使其退守连镇。次战,又用计水淹七军,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风祥。因此丰功,咸丰五年2月,僧格林沁得封博多勒噶台亲王。此时,僧格林沁45岁。
这年6月,僧格林沁再次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俘获太平军又一名将李开芳。僧格林沁威名大振。
咸丰九年6月,在抗击英法联军的大沽口保卫战中,僧格林沁率军勇敢出战,击沉英军炮艇4艘,击伤6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这是自1840年外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为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立下了功勋。咸丰十年9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退守京畿八里桥的僧格林沁率所部1万蒙古骑兵,与侵略者再次展开激战。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冒着枪林弹雨和忠勇的士兵一道拼死杀敌。但这一次,僧格林沁败了,马刀没有拼过洋枪,北京沦陷,圆明园也被一把火焚毁。僧格林沁被革职。
1865年5月,被慈禧太后看好的僧格林沁再次奉诏出山,这一次的对手是河南山东一带的农民义军捻军。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为朝廷安危在山东横冲直撞,反复进剿,他想一鼓作气消灭捻军,甚至十几天不离马鞍,最后累得双手连马缰也拿不住,要用布带拴住肩膀才能驾驭马匹。久疲之师,终于落入机动作战的捻军伏击圈中。5月18日,僧格林沁战死,那年55岁。
僧格林沁一生辅佐了大清三朝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堪为鹰獒之士。身为武将,其人忠勇刚烈,冲锋陷阵,敢为人先。咸丰帝听说他在战场上勇冒矢石的事迹后,特赐其“湍多罗巴图鲁”称号,意为急流一样不可阻挡的英雄。
僧格林沁身在清廷40年,膺亲王之爵,食双倍俸禄,多次挽狂澜于危机之时,生前身后,倍极荣耀。就连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分别迎娶的是清室贵胄女子为妻室。作为从科尔沁草原上走出来的忠勇之士,他最终实现了为大清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慈禧太后曾说:“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国亡。”47年后,清朝在风雨飘摇中终结。
僧王死的地方也叫落王座
赖文光率领的捻军与僧格林沁对垒时,赖文光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与清兵周旋。而所向披靡的僧格林沁终于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在山东前线,僧格林沁以轻骑追击,日行300里。当时有人向曾国藩汇报军情,曾国藩惊曰:“轻骑追击为用兵大忌,僧王险矣。”果然,不久前线就传来噩耗,僧格林沁阵亡。曾国藩立即派左宗棠领一万兵去战场救援。
左宗棠刚走到半路,见有人骑一匹快马背驮一个大包飞奔到面前翻身下马。左宗棠一看,来人是僧格林沁的马僮王世珍。左宗棠急忙问僧王的情况,王世珍哭着说出了僧僧格林沁战死沙场的前后经过。
当左宗棠让王世珍带路赶到战场时,只见一片惨状,尸横遍地,好不容易在乱丛中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草草地装殓在棺内。左宗棠派人仔细打听后得知,僧格林沁遇难的地方叫张家楼子,此地另外还有个名字叫落王座。
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贴身马僮王世珍把僧格林沁唯一的遗物,一顶珊瑚红顶帽带回北京的僧王府,结果被僧格林沁的儿子大骂一顿:“王爷死得起,你死不起,给我滚开,不接!”连送三次,都遭到拒绝。最后,王世珍被派到昌图任职养老,一直活到民国初期。当地人都叫他“王五老爷”。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吴大舌头”吴俊升,就是他收养的义子……
十六岁捻童杀了老英雄
曹州之战,捻军首领张宗禹诱敌深入,骄横的僧格林沁不知是计,穷追猛打,结果陷入重围。僧格林沁突围时受伤落马,藏在麦田里。一个叫张皮绠的小捻军持刀搜索残敌,他发现了身穿黄马褂、浑身是血的僧格林沁。小捻军不知此人是谁,见还有气便上前捅了一刀。当他穿着黄马褂回到军中,人们才知道他杀了清军大将僧格林沁。当时,张皮绠还是个16岁的孩子。张皮绠是涡阳北张楼村人,出身贫寒。捻军来后,父母领着张皮绠投捻,被收为捻童。
后来,张皮绠母亲病故,父兄也在军中战死,张遂离军返家,用带回的银两在龙山置地,改名为张凌云,娶妻,生一子,名张武。
同治十二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派3名暗探,化装成商贩至涡阳,寻捕张皮绠。暗探住在一家粮坊里,恰巧,粮坊老板就是张皮绠。因酒后失言,张皮绠身份暴露。暗探将其拘捕,并从他家中搜出僧格林沁的朝珠等遗物。
朝廷得知杀害僧王的元凶落网,下令将其押解山东济南,凌迟处死。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刑前,张皮绠慷慨直言,陈述斩杀僧格林沁的经过,如在眼前。
陵墓被毁 僧格林沁不是黄金头
关于僧格林沁之死,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僧王遇难后,被捻军割去头颅,身首异处,属下只抢回一具无头的身子。安葬时,清廷特选派工匠,打造了一只黄金头颅安上。
1948年夏,已安卧巴虎山下83年的僧格林沁墓,被当地农民拆毁。人们打开地宫,掀开棺椁,死去近百年的僧格林沁静静地仰卧其中,尸体尚未腐烂,身着亲王朝服,身首俱全。哪里有什么黄金头?僧格林沁尸身裸露后,随风而朽。
陵园附近的村民说,僧格林沁陵墓被毁时,珠宝玉器成箩筐地往外搬。其中有一只九龙杯尤其显眼,装满酒时,杯中会出现九条游动的金龙,引颈奋爪,状若活物,此杯后来不知所踪。有当地老人介绍,从墓穴里翻出好多的绸缎,后来都做扭秧歌的带子,用了好些年。现在,僧陵只有又重又大的“圣旨碑”未被砸毁,成为墓园的唯一遗迹。
僧格林沁王陵占地约70亩,位于公主陵村东一处朝阳的山坡上,当地人称马鞍山,系巴虎山余脉。据史书记载,僧王陵园建筑极具工巧,气势恢弘,分为内墙、外墙,前殿、后殿,几进院落;墙里墙外,松柏参天。沿山坡而上约百米,起有三个宝顶,为僧格林沁及其妻妾穴居所在。陵前有碑楼,楼内青石铺地,内中端坐一硕大赑屃,身上驮的便是同治帝所题的青石蟠龙碑。僧格林沁下葬时,同治皇帝载淳不过10岁,能否亲提碑文只有天知道。
如今,僧格林沁陵所居之地,片瓦无存,成了一片玉米地。只遗留下一块圣旨碑孤零零地立着。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不仅僧格林沁的墓地被毁,他的儿子、孙子死后的安身之所也同期被捣毁。僧王3代,生前荣华至极,死后寸骨无存。悲哉!
后人守墓 孤老伴孤碑
如今,守护着僧格林沁孤碑的是一位蒙古族农民白庆荣,今年59岁。史料记载,白家是于1761年调来为雍正皇帝的侄女和颐端柔公主守墓的蒙古族贵族。“祖上犯了点事,乾隆年间发配到法库来守墓的。”白庆荣这样解释自己家族的迁居史,“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守墓了。”
僧格林沁陵墓建在此处后,白庆荣的祖辈便开始专门守他的墓。“咱们虽说是发配守墓,但也是贵族!”白庆荣说,“咱们跟成吉思汗、僧格林沁都是一个姓。”上个世纪50年代,白庆荣的父母搬出了僧格林沁陵寝所在地。他们不会想到,数十年后,他们的儿子又一次成为这项“家族产业”的延续者。
1993年,法库县文物管理办公室找到白庆荣,在墓园的旧址旁边给他盖一间看护小房住,看什么呢?就是那块已经断成两截的石碑。
14年来,白庆荣一直与僧格林沁碑共度晨夕。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小炕头上还摆着一本已经很旧的《僧格林沁史》,多年来,白庆荣已经深深了解了他的陵墓主人。他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是,“怕为前辈守墓的行当断送在自己的手里”。
有白庆荣这样一片赤诚,若僧格林沁灵魂有知,似乎也该知足了。
没有了陵地依托的僧格林沁碑在雨雾中静静地矗立,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但愿这唯一的旧物不会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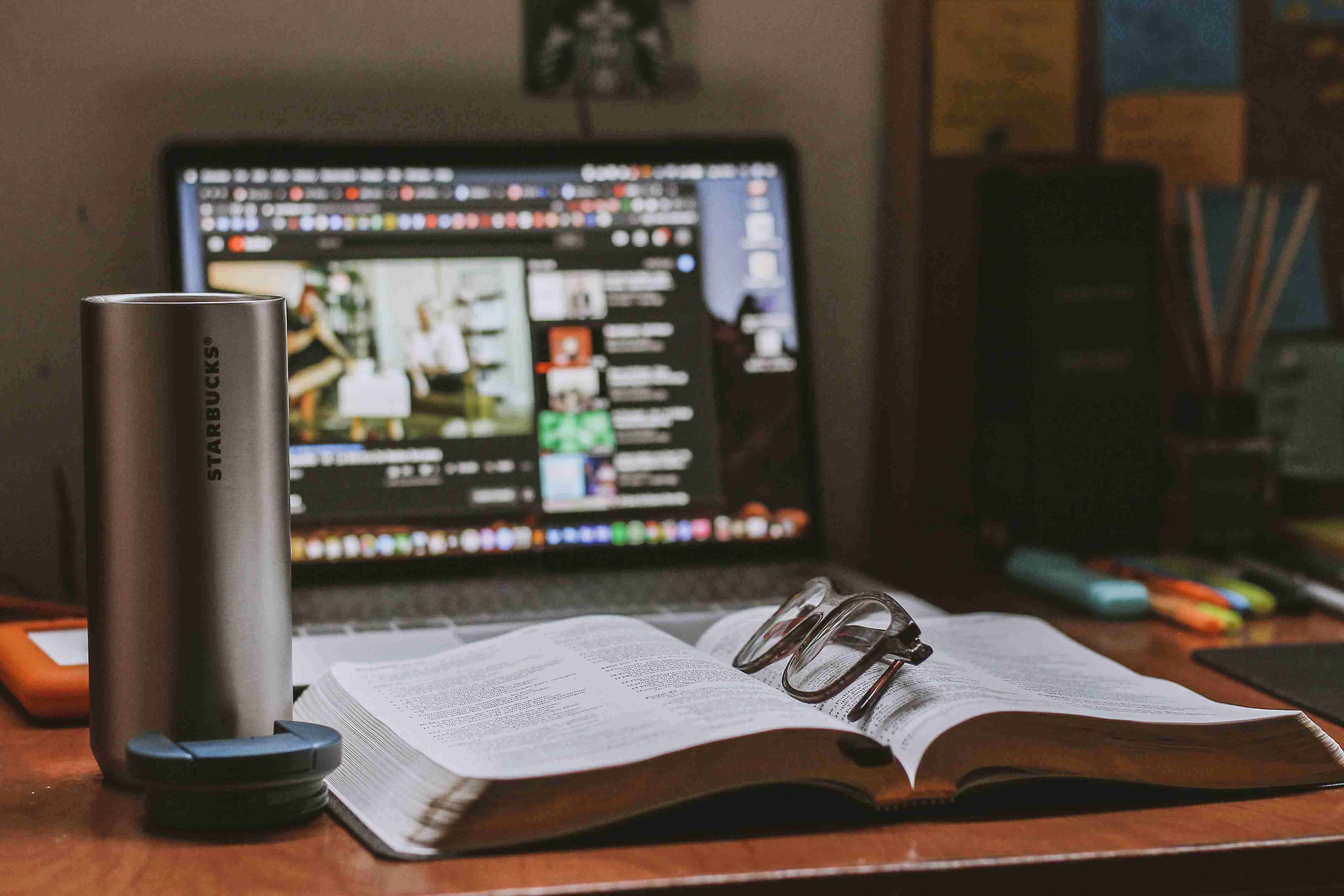
隆冬腊月,辽北天空碧蓝如洗。
这里是沈阳市法库县西北25公里,四家子蒙古族自治乡公主陵村。
一座一丈七尺高的青石透龙巨碑孤零零地指向天空,压得身下的驮碑赑屃合不上大嘴。
100余年的风雨让巨碑上同治皇帝的圣旨已模糊不清,只有依稀的几行还可以辨认:
“……荷三朝之宠眷,经百战之勋名”
“……督师五省,侵寒耐暑;临阵六年,奋爪士以同仇”
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26代侄孙——清朝最后一个敢于提刀上马的贵族大将——僧格林沁亲王,魂归于此。
一生奉三皇三年魂归路 清朝最后一个贵族大将
公元1206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召开大会,号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大弟哈萨尔的分封地在科尔沁,意为“箭簇”。1811年,哈萨尔家族的第26代孙出生,名唤僧格林沁,意为“宝狮”。
14岁那年,身为放羊娃的僧格林沁被道光皇帝看中,继承了祖辈传下来的王位。
僧格林沁像祖辈那样,用骏马和钢刀镇住了摇摇欲坠的晚清统治,也蒙受过痛彻心肺的奇耻大辱: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已经打到京津城下的北伐军;在大沽口击沉英法联合舰队的4艘炮舰;在北京抵抗英法联军失败……他与曾国藩齐名,号“南曾北僧”,而曾国藩则说:“在抵外侮又剿内匪的过程中,(僧格林沁)其功远远在我之上。”
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在山东征讨农民军的战斗中阵亡。从此,满朝的王公权贵再也没人敢于提刀上阵了,直到清朝灭亡。这正应了慈禧太后之言:“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国亡。”
曾为道光送葬,并保住咸丰帝位的僧格林沁于同治时期兵败身死,满朝震动。同治帝下令:在僧格林沁的家乡为他建造一座墓园。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史料记载,足足用了3年时间,僧格林沁的陵园才最后落成。占地70亩,备极哀荣。三座大陵墓,分属于僧格林沁及其正妻、侧室。
七十亩墓园寿断风雨中 历经天灾人祸的百年
时光如水,岁月悠悠。僧格林沁墓园,终于没有熬过百年风雨。
自打墓园建立,法库当地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僧格林沁的人头被农民军割去,棺内是用黄金打造的假头。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当地人“为破除封建迷信”打开了地宫。
“听我父亲讲,当时珠宝玉器成箩筐往外搬……绸缎都做成秧歌带子了。”当地一位温姓蒙古族农民回忆,只有又重又大的圣旨碑未被砸毁,成为僧格林沁墓园惟一遗迹。让农民们大失所望的是:“黄金人头”纯属子虚乌有。死去近百年的僧格林沁静静地仰卧在红松棺材中,尸身未腐。
“常听长辈们说:这么些年了,尸首还没有烂,肯定有些特别的技术在棺材里面。”70多岁的当地蒙古族农民白明儒回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僧格林沁碑又遭了“天灾”——一夜雷雨之后,碑的上半截断了,直接向前倾倒,正好砸到驮碑的“大龟”——赑屃头上,双双断作两截。
幸好当时的法库县县长极具文物保护意识,指示一定要重修复原,这才使历经百年风雨的僧格林沁碑得以幸存。
记者看到,从圣旨碑到赑屃,处处可看出青石混合水泥的修补痕迹,赑屃的下巴就是用水泥铸成的。
发配来守墓“贵族心”不改 第十代守墓人55岁
长脸,络腮胡子,深深的抬头纹砍在额上,略微弯曲的一对凤眼,头上盘着一团弯曲发亮的黑发,棉裤毡鞋——这就是55岁的当地蒙古族农民白庆荣。
“原先姓包……因为犯了事,在乾隆年间从科尔沁左翼后旗发配到法库来守墓的。”白庆荣这样解释自己的家族迁居史,“到我这一辈,正好是第十代。老辈人说了,要是哪天皇上一开恩,还能让咱们改回包姓。”
史料也记载,白氏家族是于1761年调来为雍正皇帝的侄女和颐端柔公主守墓的蒙古族贵族,如今已成为当地最大的姓氏。
僧格林沁陵墓建在此处后,白庆荣的祖辈便开始专门守他的墓。“咱们虽说是犯了事被发配来守墓的,但也是贵族!”白庆荣说,“咱们跟成吉思汗、僧格林沁都是一个姓!”(蒙古族黄金家族姓氏“孛儿只斤”后汉化翻译为“白”等姓氏——编者注)
这个家族的衰落,始于第八代,也就是白庆荣的爷爷。其过程很像电影《活着》。赌博、吸毒,他只活了45岁,就把祖辈传下来的封地一块块分割卖净。至死,白庆荣的奶奶还对老伴记恨不已。1952年,白庆荣出生。
晨起忙干活晚看电视剧 “我在网上也算个名人”
事实上,白庆荣只会说简单的蒙语,“吃饭”“喝水”;惟一一次骑马,是年轻时在生产队骑的犁地马,差点摔下来——祖先纵马草原的生活痕迹在他身上已经近乎完全消失。
上个世纪初,白庆荣的父母就搬出了僧格林沁墓园。他们不会想到:数十年后,他们的儿子又一次成为这项“家族产业”的延续者。
1993年,法库县文物管理办公室的两位主任——张兴华和魏春光找到白庆荣,许给他如下条件:墓园旁边给他盖一间看护小房住,每月再加80块钱的工资。双方签了一份《守陵合同》。几年前工资涨到了100元。
“他们这个家族从古代起就是专门守墓的……现在他来干,也算是继承祖业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兴华若有所思地说,“只不过现在是出自另一层意义——文物保护。”
14年来,离异的白庆荣一直与僧格林沁碑相依为生。父母早已去世,只剩他自己住在这座小房里。从他父亲年轻时起,就搬出了世代居住的陵园;如今他又搬回去了。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看看电视剧。僧格林沁家乡的县委书记、北京的文物爱好者、中央电视台记者都给他留下了自己的名片。“他们说,我在网上也算个名人。”白庆荣咧嘴乐了。
一代草原雄鹰归息的地方
魂兮归来
公元1865年7月的一天,一队扶柩北归的队伍自北京城出发,一路缓缓而行,最终目的地是今天的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车上殓载的人物是被大清国“倚为长城”的博多勒噶台亲王、科尔沁左翼后旗第十代札萨克(旗主)僧格林沁。
魂兮归来,北归的路上,风吹草低,胡笳呜咽,沿途官民肃容降迎。
3个月前的5月18日夜,在山东省荷泽地区高楼寨吴家店镇的一块麦田里,率7000蒙古骑兵追剿捻军张宗禹部至此的僧格林沁,误中埋伏,《清史稿》上说其“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辩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终年55岁。噩耗传至北京,同治帝为之号啕,“方期天鉴忠忱,克竟全功,长承恩眷,乃猝遇贼伏,力战阵亡。览其死事情形,不禁为之陨涕。”为此,同治帝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还与两宫太后亲临府上赐奠,“予谥曰忠,配飨太庙,绘图紫光阁。”
谥曰忠,是对忠勇、刚烈,对大清国忠贞不渝的这位科尔沁蒙古族勇士恰当的评价。
僧格林沁,姓博尔济吉特氏,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26世孙,黄金家族血统,出生于今天的内蒙古通辽市科左旗双胜镇,少时家境贫寒。15岁时,经在雍和宫当喇嘛的伯父暗荐,承嗣了其远房亲族——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世札萨克、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而索王之妻,便是道光皇帝的姐姐。穷孩子一步登天,从此,僧格林沁的人生伴随着大清国的国运,开始了他倍极荣辱的生涯。这一年的12月,15岁的僧格林沁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24岁时,被授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25岁时授镶红旗蒙古都统,成为统领一旗之士的年轻将领。道光30年(1850年),40岁的僧格林沁奉命在京郊密云县剿匪,此战,僧格林沁谋篇布阵,亲冒锋镝,一举剿灭悍匪,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华。
咸丰3年(1853年)8月,对清庭构成巨大威胁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京畿重地的周围,9月,咸丰帝亲自将“纳库尼素光刀”授予僧格林沁,命其率军进剿。这柄刀非同寻常,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遗物,干重之意,不言自明。不负众望的僧格林沁,先是率军在天津南的王庆坨一战击溃林风祥部,迫使其退守连镇,次战用计水淹七军,生擒林风祥。咸丰5年2月,恩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4月18日,再恩诏世袭罔替。此时,僧格林沁45岁。同年6月,僧格林沁再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
咸丰9年6月,在抗击英法联军的大沽口保卫战中,僧格林沁率水陆军兵,勇敢出战,击沉英军炮艇4艘,击伤6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这是自1840年外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为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咸丰10年9月21日,退守京畿八里桥的僧格林沁及所率1万名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再次展开激战。清军手持长矛、大刀“悍不畏死”,一次次向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发起攻击。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悲壮的一笔:八里桥上,抱定必死决心的僧格林沁,骑着心爱的战马,不顾身边尖啸而过的弹雨,和部下的勇士拼死与敌对决着,身边威武的旗手手擎黄地黑字帅字旗,和主人一样小山般在桥上挺立着,一颗炮弹飞来,旗手倒下了,握紧大旗的手痉挛着,眼睛怒视着前方。就连僧格林沁的对手——法军指挥官吉拉尔,在《法兰西与中国》一书中,对清军的英勇也做了充满敬意的陈述:没有害怕,也没有怨言,他们甘愿对大家的安全而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然而,僧格林沁败了,大清的国都沦陷在英法联军手中,圆明园也被一把火焚毁,“巴图鲁”式的勇敢,终不及现代兵器的威力。
西风残照圣旨碑
1865年的5月,因战败被夺爵的僧格林沁再次奉诏出山,这一回的敌手是捻军。被同治帝谕为“忠勇性成”的僧格林沁,率蒙古旗兵在中原大地上“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3千余里”,一如继往地为保卫大清的江山冲杀着,甚至10几天不离马鞍,最后累得双手连马缰也拿不住,要用布带拴住肩膀才能驾驭马匹。而这正犯了兵家大忌,久疲之师,终于落入蓄势而战的捻军伏击圈中。
有一种说法,僧格林沁兵败被围后,“乃下马踞坐于地,示诸军无退意,匪亦不知其王也,然围之甚急,王恐为贼所得,乃从容就义。”这是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述的。还有一种说法,僧格林沁败走麦田时,捻军中一个叫张皮绠的16岁小战士,在搜索中发现了时已身受重伤的僧格林沁,遂上前杀之。此说见于《太平天国史》。在当地还有一种民谣:“张皮绠、真正强,麦稞地田里杀僧王。”
僧格林沁死于张皮绠之手似是真的。8年后,山东巡抚丁宝桢经过密访,抓获了已经是一家米行老板的张皮绠,并在其家中搜出一串僧格林沁所戴的朝珠。不过,此时的张皮绠已改名为凌云,娶妻生子,其子名叫张武。张皮绠死时慷慨直言,陈述杀害僧格林沁的经过,如在眼前。张皮绠杀死僧格林沁后,就离开义军回到老家涡阳,用积攒的银两在老家买了一块田地,改名换姓,娶妻生子,还在集市上开设粮坊做点小生意,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张皮绠酒喝多了,谈起了当年杀死僧格林沁的英勇往事。巧的是,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正派人到这一带搜捕张皮绠。丁大人获得了这一信息,就将张皮绠逮捕。
1873年,张皮绠被押解到山东济南,经过审讯后,遭到凌迟处死。时年24岁.
失“柱石”之痛的大清国这一对“孤儿寡母”,对僧格林沁恩恤有加,著僧格林沁的儿子伯颜纳谟祜承袭王爵,孙子那尔苏赏为贝勒,世袭罔替。凡僧格林沁征战过的地方如河北、山东等5省之地,皆建忠王祠,以示悯恤,并在北京专修一座显忠祠,在僧格林沁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今辽宁省昌途县再建一座僧王庙,其战死的地方吴家店,也改名为落王庄。同治帝还诏谕:著赏给陀罗尼经被,照阵亡以亲王饰终,准其入城治丧。其灵柩返旗时,著沿途地方官员妥为照料,并派乾清门侍卫专程护送。
魂兮归来,北归的路上,车马萧萧,但没有了厮杀的刀光剑影,多的是一抹夕阳残照。
僧格林沁一生辅佐了大清三朝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堪为鹰獒之士。身为武将,其人忠勇刚烈,冲锋陷阵,敢为之先。咸丰帝听说他在战场上勇冒矢石的事迹后,特赐其“湍多罗巴图鲁”称号,意为急流一样不可阻当的英雄。身在清庭40年,膺亲王之爵,食双倍俸禄,多次挽狂澜于危机之时,生前身后,倍极荣耀。就连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分别迎娶的是清室贵胄女子为妻室。作为从科尔沁草原上走出来的忠勇之士,他也实现了为大清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为僧格林沁选择的墓址是一个背依青山,脚踏泉水的吉祥之地,就在肥美的科尔沁草原左翼后旗领地、一座名叫巴虎山的地方。巴虎山,蒙语,兴盛的意思。山脚下,同治皇帝御题的青石盘龙巨碑傲然耸立,其碑高一丈七尺,合5.66米,碑首刻圣旨二字,碑身上书大清同治四年乙丑十一月二十日建。碑文为同治帝手书,用满汉两种文字篆刻而就,全文310字,记述了僧格林沁的生平和战事。
慈禧太后偿言:“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国亡。”想来,慈禧所言非虚,僧格林沁统率的是大清国最后的精锐之师,吴家店之战后,满蒙铁骑不在,大清军队的统辖权,也渐归汉军中的曾国蕃、李鸿章等人所属。昔日的“南曾北僧”,成了南曾的独角戏。又过了47年,大清国也在风雨飘摇中终结了。
陵墓被毁,出土僧王尸身俱全
关于僧格林沁之死,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僧王遇难后,被捻军割除去头颅,身首异处,属下只抢回一具无头的身子。安葬时,清庭特选派工匠,打造了一只黄金头颅安在颈项上。
1948年夏天,已安卧巴虎山脚下83年的僧格林沁墓,被时为解放区土改政权捣毁,一代草原雄鹰重见天日。据僧王陵世代看坟人白明儒所见,僧格林沁出土时,身首俱全,面相厚重,皮肤尚有弹性,身高约1.72米左右,有蒙古族人的体貌特征。其身着青布夏装,两层夹衣,左右胸前肩窝处各有一处刀剑创伤,长约10厘米,伤口呈黑紫色,此外,身体其他部位也有多处明显伤痕。尸身裸露后,既随风而朽。白明儒今年76岁,这是他小时候的记忆。同时看到这一幕的还有村里的前任支书刘景材,今年74岁。两位老人亲身所见,当为不虚。
据当地其他老人说,僧格林沁墓被毁后,墓中出土了大量陪葬品,其中有一只九龙杯尤其显眼。装满酒时,杯中会出现九条游动的金龙,引颈奋爪,状若活物,此杯后来不知所踪。
僧格林沁王陵占地约70亩,位于公主陵村东一处面阳的山脊上,当地人称马鞍山,系巴虎山余脉。据史书记载,僧王陵园建筑极具工巧,气势恢弘,分为内墙、外墙,前殿、后殿,几进院落,墙里墙外,松柏参天。沿山脊而上约百米之处,立有三个宝顶,为僧格林沁及其妻妾穴居所在。其陵前碑楼,高三丈余许,四周各有券洞门,楼内青石铺地,上雕波浪纹,内中端坐一硕大赑屃,头至尾全长3.3米,高1.23米,最宽处1.35米,四足撑地,头颈高昂,张口瞪目,似有向前之势,其身上驮的便是同治帝所题的青石盘龙碑。
如今,僧王陵所居之地,片瓦无存,只遗留下这块圣旨碑,半山坡上,两只跛脚的石狮子歪在一侧,向世人诉说着苍桑,狮子的前腿已被砸裂,陵园也成了一片玉米地。2011年4月12日,记者再次前往四家子乡探秘僧格林沁王陵时,同行的僧王陵守坟人白明儒和侄子白庆荣凭记忆,在山上一处已翻耕好的地垅沟里,插入一截玉米杆,然后指证说,主墓穴位置就是这里,另两个分列左右。记者看到,由于年代久远,原来留下的深坑渐被填平,地上只留有模糊的凹陷痕迹。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不仅僧格林沁的墓地被毁,与他同归科尔沁故里的儿子伯颜纳谟祜、孙子那尔苏,死后的安身之所也同期被捣毁。其实,僧王祖孙3人安息之地相隔不远,翻过巴虎山,进入康平县的东升乡善友屯村就是。谁能想到,生前荣华至极,死后寸骨无存。
百年未见,十八只雄鹰在天空翱翔
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僧格林沁死后,在他的家乡科尔沁草原上,流传着上百首传颂他的英雄事迹的民歌,其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嫩江十旗为羽翼
大漠南北为僚佐
攘外安内的僧王爷
威震四海重竹帛
……
从这首民歌中,我们能感受到僧格林沁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早在几年前,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曾来恰商要请回僧格林沁的灵宝,重新立坟安葬。对方态度诚恳,出多少钱都行,被时任四家子蒙古族乡乡长的白云波拒绝了:“那样做,我就是四家子乡的千古罪人!”
热爱这块热土,具有文物保护意识的白云波,稍后既动用人力将散落在山上的僧王陵石狮修复,并搬请下山,重新安放在山下的碑亭前。
2009年11月9日早7点,巴虎山上云气葱郁,一缕寒霜给往日沉寂的山村铺上一层细碎的银花。石狮揭幕仪式即将举行。市、县蒙协的领导来了,仰慕草原英雄僧格林沁的人来了,公主陵村的男女老少也都来了。一杯马奶酒,奠慰英雄魂。早7点40分,揭幕仪式开始。随着一围蒙在石狮上的红布徐徐拉开,在场的人们肃容以对,以示心中的敬意。此时,天空中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一队雄鹰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排着整齐的队形在陵前上空盘旋,吻、翼均清楚可见。一只、两只、三只……一共出现了十八只,这是巴虎山上的雄鹰啊,是草原吉祥的象征!人们数着、喊着,激动万分。据村里老人讲,天空中出现一、两只雄鹰不奇怪,同时出现十八只雄鹰的场面,百年未见。此时,距僧格林沁死去已1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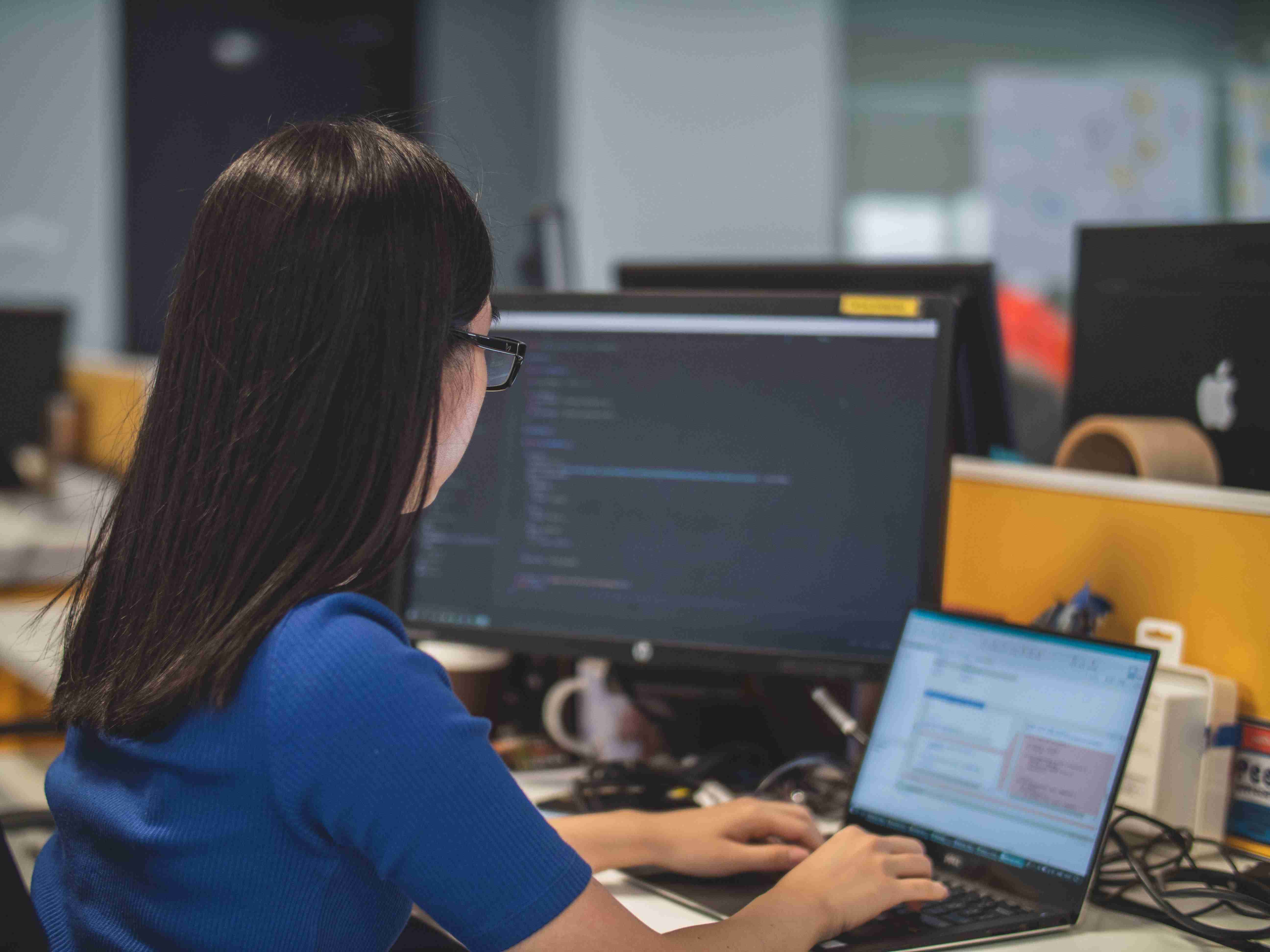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